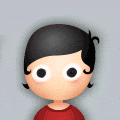开学三个星期后,一天午后。于思文正在上课,外面天暗了下来。校长进来,通知停课,说有大暴雨,让孩子们赶在涨水之前赶回家。还叮嘱“晚上不要睡得太死,听到垮山的声音,赶快跑”。
疏散掉孩子们,于思文和奈维跟大家一起布置学校防汛措施:把一楼的贵重物品搬到二楼,把课桌椅堆在角落里,用绳子绑在一起;检查二楼的门窗,松动的、破败的,都用木条、木板钉上。
忙完,天快黑了。校长、老师、校工们也都赶回家去了。于思文拿一把伞递给奈维,说:“你快回去吧,当心大雨回不去。”奈维看着于思文,笑了笑,说:”我家在山坡上,地方高,从来没被淹过。学校每年都会进水。”于思文听出奈维的言下之意: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
又停电了。幸而奈维早有准备,储备了一包蜡烛,一个酒精炉子和一包酒精燃料块,还有足足一个多星期的食粮。奈维把锅碗瓢盆从阳台搬进房里,关好房门,点上了蜡烛,开始做饭。
风来了;山谷中似乎万马奔腾。雨来了;大滴大滴的雨点,喧嚣嘈杂的击打着门窗。两人就着烛光,一起吃晚餐。突然间,“啪”地一声巨响,然后袭来一阵狂风,吹灭了蜡烛。原来是阳台一侧的一扇窗户被吹开了,玻璃碎了一地。接着,那扇窗户被狂风反复地开、关,啪啪地巨响,让人胆颤心惊。
奈维摸着黑,重新点燃蜡烛。让于思文一手握着蜡烛,一手护着火焰。就着烛光,找到锤子、钉子和一块塑料布。让于思文跟在后面,开门到阳台上。顶着风雨,把窗框钉牢,把塑料布钉在窗框上;暂且用来挡雨。
风突然改变方向,吹灭了蜡烛。于思文对奈维说:“你等着,我去找打火机。”奈维说“不用了,已经钉好了。”扔下锤子,拉起于思文,抹黑回到屋里。
风很大,两人费了很大劲才关上们。于思文转身,正要摸到书桌去找打火机;突然被奈维从后面抱住,感到耳边一阵灼热的呼吸。于思文呆了一会儿,握住了奈维颤动的手臂。奈维感觉到了于思文的默许,开始吻于思文的耳廓,然后是脖子,一路滑到肩膀。于思文全身掠过一阵轻微的颤栗,掰开奈维的胳膊,转身抱住奈维,吻起来。
不知过了多久,奈维抱着于思文,摸着黑,磕磕碰碰挪到床边,顺势倒下,压在上面。一面吻于思文,一面将于思文的手牵引到那儿,握住自己。时不时一阵剧烈的痉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奈维猛然一吼,低沉、压抑,却又极富穿透力,骤然倒在于思文身上。过一会儿,奈维翻身,让于思文压住自己,握住于思文,直到于思文释放。
那次暴雨不停歇地下了一个多星期,水淹没了操场,淹没了一楼教室,直到十多天后才退去。然而那十来天,却是于思文这辈子最为宁静无忧的日子:两人与尘嚣彻底隔绝,唯有彼此。一起看洪水、做饭、吃饭、聊天、唱歌、读书、画画 …… 没有电,就点蜡烛、燃柴火;没有水,就接雨水,洗澡就是在阳台或者走廊上淋雨;到最后,没有了吃的,就找个竹竿、绑上网兜,在洪水中捞鱼。这样简单、原始的生活,反倒别有一番情趣。
于思文突发灵感,画了好几幅画。在阳台或走廊支起画架,画大雨,画洪水,画闪电;奈维在一旁打伞遮雨。阳台对着街,街上大雨漫灌,水没到行人的腰部;走廊对着操场,操场外是河,河水从平常的清澈透明变成了浑浊的土黄色,在大雨中,在闪电下,咆哮着,翻滚着。在于思文看来,这大雨,洪水和闪电,湮没了一切尘嚣,勃发出一种振聋发聩的能量。有生以来第一次,于思文感觉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