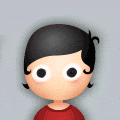在男人看到女人那张黑着拉长的脸,女人的眼神如路人,冷冷的丢下一句话,事情你看着办。
男人觉得自己在心里,又死了一次。
父亲刚放下手中的手推独轮车,麻绳织的扣肩还一头搭在父亲的肩上,一头缠绕在独车轮的把手上,两个小时的山路,一缕花白的头发被汗水打湿,黏在额头。看着儿媳的离去,父亲扯扯衣角,嗫嚅着嘴,说你妈非得来,说给你送两袋新鲜的,刚下地的麦子过节。
父亲做了一辈子民办教师,在要有转正的机会时,说不符合政策,年纪超了几岁,黯然到最后被清退了。几年过去,拿了一辈子粉笔的手,在男人眼里,父亲的手忽然和麻绳般粗糙。
没事,男人拍拍父亲的肩,扛起麦子,踏步前行,一低头的瞬间,耸耸肩,带去了眼里含着的晶莹,男人不愿让父亲看到。
母亲欢天喜地的招呼着怯生生不敢靠前的孙子。母亲肩头还挎着当年他上学时的背包,有几个补丁,母亲说父亲不舍得扔,父亲又说是母亲不舍得扔,包里鼓鼓囊囊的,男人知道,父母又把攒着稍微好一点的生活捎带给他,如当年给他辛苦的攒学费。她就这样望着母亲,母亲手里捧着一大把村东头小卖部买的糖果,孙子依然躲在姥爷的背后,不肯出来,母亲回过头,茫然的看看男人,又移向父亲,不知所措。
男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,利落泼辣的母亲遇到难题时,总这样望着父亲,以前,父亲总是紧走两步,边走边说,没事没事……
父亲今天也突然失去主张,张着嘴,在那棵桂花树下木然着。
在城里什么没有,隔窗的声音虽然尽量压力,男人还是能想象,岳母那撇着的嘴。六岁的儿子只每年回过一次老家,平时女人不让带孩子回,孩子也不肯去。在男人坚持时,姥姥总是来圆场。结果男人只能一个人回家看望村里的父母。
男人记得最长时候那是女人坐月子去了村里,还有就是结婚,生孩子时赶上岳父好像出了点事情,城里日子也不好过,没有人照顾。女人回了乡下,那段时间,周末,男人回到山村,总感觉,母亲的青春回来了。踮着脚,早晚的忙到黑,声音脆脆的。父亲刚从小学退回来,收拾着家里的庄稼地,笨拙的蹲在厨房的角落,切着早起扯的菜叶,然后伴好着鸡食,打着猪草,不时的帮母亲添一把灶上的柴火,父亲偶尔回头看他的眼神,有许多光彩。
这些光彩,因为女人的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后,一点点的消逝。如火灾后微弱的光,星星点点,逐渐的依次消失。女人也再也不回村了。
每次回村,男人都不去看父母的表情,儿子不愿意回来,父亲母亲老早就在村头等,神情便一次比一次黯然。在城里的家里,父亲母亲是不被计算在内的,因为儿子分糖果时,妈妈,姥姥,姥爷,爸爸,没有爷爷奶奶,男人这时候的心里,环顾四周,尽管房子最后还是自己买了,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。
每次都是父母亲自己主动说起,反倒来安慰他,没事,好好过,孩子大了就懂事了,会回来的。男人后来坚持买这套房的原因,女人是不知道的,因为旁边这条河,像极了村头的那条河,在城市的边缘,这或许给了男人很多故乡的温暖,每次临窗,男人都会想,那些洗衣的老妇群里,会有着她的母亲。那些江边闲逛的老汉中,也有他的父亲。
即使这样想象的场景,男人也觉得给了自己一些生活的温度。
岳父母说要照看孙子,卖了自己的房子,搬了过来,回村时,和母亲说起,母亲说,这样也好,孩子有人看,他也不知道说什么,低头去洗脸,一回头,他却发现,揉着面粉的母亲,偷偷用系着的围裙擦着眼睛。
村里人说,风儿他娘可是村里一只花,事事要强,里里外外一把好手,就是命差了点,男人窝囊一辈子,到老也是个赤脚老师。好不容易苦熬吧日子,给别人养儿子。
风儿是男人的小名。
男人聊起这些,母亲说,村里人说笑哩,哪家没有个三长两短的,你爹人好着呢,他们不懂。在城里,你好好过日子,看好小宝,娘值咧。
男人知道,父亲是个内秀的人,回来后的父亲,闲时帮人刻着墓碑的字,写的很端正,如印刷一样。
有时,回乡远远看父亲母亲依偎在窗前晒太阳,他眼睛里就潮湿。
母亲依然愣在那里,一瞬间,男人忽然差异自己竟然想起如此多的画面。后边,是跟着推着独轮车的父亲,不用回头,他也能想象父亲的脸,短短几年,父亲的灰白头发多了很多,如童年教室里飘扬着的粉笔灰。
那时的父亲,在破旧的山坡,简陋的教室,那一批批的孩子,父亲意气风发的领读,仿佛带着浸在苦难中生活的人重新走向新生,父亲的脸上一片圣洁。
那时,父亲也就是他这个年龄,母亲麻利的帮父亲张罗里里外外,穿梭在院里,山坡,村头,田间。都说母亲是父亲的蝴蝶,因为,父亲娶母亲,只有那件翠花小棉袄是给母亲唯一上台面的家当,男人叹口气,觉得自己和头发花白的父亲一样的沧桑。
男人觉得母亲是父亲的蜜蜂,不断的采蜜,家里渐渐不再四壁徒凉,母亲的巧手和父亲的好脾气,让男人的童年,少年都很实在。
山外的世界就是不一样。
要过节了,女人说,今年爸爸说在城里过,男人没有吭声。他在想,母亲和父亲在村头张望的由热切转向失望的脸。
忽然的,父亲母亲就这样过来了,男人心里很开心,觉得这才是生活。可是生活有许多事情要面对。
男人走向前,孩子被不情愿的带到奶奶身边,身子还是向后躲的。
亲家,家里什么都不缺,以后,大老远的,不麻烦了。
丈母娘出来,甩甩手上的围裙,掸着裤子上并没有的灰尘,如墙头扑腾挑下的鸡,抖抖蓬松的羽毛。
岳父一言不发,紫黑的唇如上锁的门的扣环。
男人忽然挺了挺腰,大踏步抱着孩子,牵着母亲,进了房间,放下,回到院里,取毛巾,给父亲卸下麻绳肩扣。父亲接过毛巾,揩着汗,告诉他姐姐写信说今年也不回来过节,厂里要值班,工资比平时多。
这一切,男人的同学看在眼里。
毕业因为岳父的关系留城后,男人渐渐和同学都没有了往来,即使是本城的,更别说外地的了,偶尔有同学聚会,男人都不去,也有仔细找到他消息的同学捎话,不去的次数多了,大家也就淡然,每个人,都有自己的生活。男人心想,就在自己的窝里这样过吧,男人不愿意和人提起家事,很多的关系。
男人的这个同学是男人大学最好的室友,上下铺,彼此话都不多,心细而敏感,来自差不多的家庭,在学校时对男人很仗义,如兄弟。常和他一起走山路看村里的父母,一起渡过困难的日子,毕业后同学去了深圳闯荡。
男人忽然很无言,同学最后帮着送父母走了,如当初在学校帮他一样。
半夜,男人醒了,是梦,父亲的叹息还在……
男人又睡了,是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