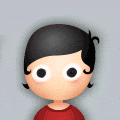坐在靠窗的位置,他穿的很干净,浅灰的休闲棉袄,黑色衬衣,打了领带,大格子的围领搭在椅子的扶手上,面容依旧很安详,只是多了一份落寞。
我在快要下班回家时接到张老师的电话,明天就是平安夜,最近负责单位年会的事情,加上到年底了,林林总总的总结和计划,各部门的工作是要年终盘点的,所以有些忙,星期六也来单位看看,记得前两天答应爱人去看场电影,是最近要上映的〈〈云水谣〉〉,很多年了,没有去看过电影,心里多少还是有愧疚的
张老师说,我想和你谈谈,可以吗,其实我可以拒绝的,我和张老师有过一面之缘,是在一位退休历史老师家里,没怎么交谈,只记得好象是面容祥和的老人。我还在思考,张老师说,我知道你的故事,也看过你写的文章,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话。你的历史老师是我多年的朋友。
我终于答应了,地点在历史老师家不远的麦当劳,去之前我还是给老师打了电话,讲了大致的情况。
上海这两天的天气不好,阴冷阴冷的,好象要下雨的样子,考虑到老人家不方便,于是把地点改在张老师家附近,就在那小区的茶馆。我到的时候,老人家已经在那里等了,其实他的事情我大致的从老师那里了解了大概,我不知道他要和我谈什么。
目光一直看着门口,见到我时,微微欠身,我们要了一壶龙井,其实在一进门的刹那间,我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有些挣扎,我是否该来,他只是我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
“我找你,是因为常听你的老师提起你,知道你是个真诚的人”我没有去打断他的话,其实从我的角度讲,他只是需要倾诉。
他说他毕业于早年的纺织大学,也就是现在东华大学的前身,主籍浙江余杭,文革其间是上海公安系统的文职人员,他的领导对他很好,,我相信他那个时候是很让人喜欢的,后来领导被揪斗了,不知道他和领导的事怎么被逼了出来,因为这件事闹的很大,他在公安系统没办法呆了,只有去了纺织系统,也就是轻工业部,因为学的是纺织贸易,其中多亏他父亲的多方周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渐渐的许多事情不了了之了,那时他已经有了他的第一个孩子,六岁,如今孩子三十六了,还没有成家。和他几乎是水火不相容。前不久搬出去住了,两个女儿对父亲也不理睬。
他的目光一直看着窗外,仿佛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其实我真的不知道,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,我就这样安静的听着,他突然停下,说的话是让我半天没有缓过来:那个农场很安静,余先生和老葛终于可以安静的睡了,只有我们,还在思念里生活。
他忽然问我,你那先生是否叫余恒之,见我鄂然,他说:九月二十五日是他的生日,你那>我看了,我知道你写的是余恒之,我也知道老葛,葛天荣,后来是第八分厂的厂长,我约你出来,是想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事情,如果你真的很想纪念他的话。
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转变,一时之间我无法言语。他说其实我不需要你的答案,因为我和你一样,在心里想念着他。
他的眼里忽然满是泪光。
他的面容依然安详。
“他是个好人,也是个可怜的善良人。”这是张老师对余先生的评价。
“我也一直在关注你,通过你的历史老师了解你的过去。”
单位忽然来了电话,台湾传过来标的方案,我必须赶回去签收,由于时间的关系,更确切说,是事情太突然,我只能和张老师另约时间在谈。我送他回家,就在这个小区。很简洁的两室一厅的房子。醒目的是两排的书柜。
“老葛一辈子也没懂什么是同志情,他是个简单快乐的人。不象我们这么苦恼了一辈子,学不会忘记。“张老师关门时对我说。
我似乎又听到老葛头在我家洗澡时说到余先生时快乐而单纯的样子。
世界真的很小。
我立即掏出电话,打给我那退休的老同事。那位历史老师,同时间返城的上海知青。
回单位办完事后,司机送我去上师大。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刚走到东大礼堂的拐角处,历史老师边围着围领正急速走向向校门,看到我,头也没抬:“快,去老张家。”
车几乎是已冲的速度返回浦东,历史老师不断的问我:“你和老张说了什么,他在电话里痛哭,回到上海十几年,他从未这样。他有高血压,不能太激动。他只有我这个朋友。”
我从位见过历史老师这样慌张,语气急躁,而我却真的是不知从何说起。在见到老张时,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我两个小时前谈过话的他了,斑白的头发乱,通红的眼睛,没有从容的神采,老人是真的老了。只有客厅开着灯,卧式没有灯,开门时,老张再次见到我,意外,要倒水,历史老师让我扶他进卧式,开了灯,我一眼看见摊在床头的书<<约翰。克里斯朵夫>>,很旧,却看的出主人的精心保存,历史老师用很快的速度把扉叶盖上,我还是看到那几行字:“相期渺渺,君当珍重。”
落款是“余恒之”,力透纸背。
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历史老师曾经阻止我写《1960年的农场和邹部长》。因为老张是当事人之一,他不能受刺激。
“老张,都几十年了,你又何苦?”扶着老张躺下,历史老师帮老张捋捋头发"咱们虽然老了,却还有日子要过,对不对,我们没办法选择,那是社会的错,不是我们。”
“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恒之被带走的样子,浑身是血,是我害了他。如果我老婆不去揭发,他不会客死他乡,落叶归根,他做梦都想回上海。”老张只是自己说着话,仿佛房间还是他一个人。
我过去帮老张掖好被子,换了杯桌上的开水,“如果您不介意,您可以讲给我听。”我阻止了历史老师想要说的话,有的时候,人是要倾诉的,哪怕对过去痛苦的回忆。
空调房其实不冷,张老师还是坚持让我和历史老师坐到床上去。我握了握老人的脚,还是冷的,于是,我先把自己手搓的更热些,然后慢慢的帮他捂着,我告诉他,高血压晚上泡热水脚时,可以按足三里穴,对高血压有缓解作用,老张渐渐的平静下来,象个听话的孩子,在帮他捂热了脚之后,老张让我坐在他的旁边。我看到历史老师感激的眼神。其实我一直知道历史老师在照顾着老张的生活,当年为了他能回上海,老张几乎把相关单位的门坎踏破。
这就是现实和理想的残酷与真实,当年一个号召,千万的知识青年走出上海,上山下乡,当他们耗尽青春时,上海已不是他们的家。回家的路困难重重,遥不可及。
共同的苦难和经历让他们的人生丰满而厚重,望着这对真挚的朋友,我忽然有了久违的感动,很多年前,在那个农场,我和老葛,还有余先生,很多风雨的晚上,我们这样拥被而坐。只是老式大木床换成宽大的席梦思让人感到时代的变迁。
很多时候,我会觉得自己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春天,所以我在聆听别人时,也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想找回自己。过去的毕竟过去了,只有现在和未来对于我们更为重要。
房间里很安静,我在心里,守了他三十年"老张的回忆朦胧而酸涩……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十年的时间,恒之象人间消失了,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消息,也没有人知道他被送到了哪里,可是,他浑身是血的样子在我心理定了格。”
我明显的感到我的心在疼,就如我看过国家遣送制度的终结后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,哪些不白之冤而死的人,留下的是亲人没有希望的上访和无尽的思念。
毫无疑义的婚姻爱人固执的拖着,是的,在那个冰冷的年代,他的爱人赢了,只有孩子可以栓住他,却也输掉了各自一生的幸福。很多家庭是这样的,谁的责任谁的错?
98年爱人走的时候,很平静的说,刻骨铭心的爱他,也恨他。
是报应吗?我没有办法回答他,他说他最近十年来,就在回忆里生活。除了历史老师,没有朋友,没有温度。孤独而倔强的活着,让我想起影片《安居》里的老人。
“因为恒之叫我要活着。”他不断的重复这句话。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。
就在这样的叙述中,他渐渐的睡了,紧紧的握着我的手,其实,说什么不是很重要,很多人在你的生命里是你无法忘记的那盏灯,几十年如一日。
离开时,历史老师送我到门口“谢谢你,是你让他开始愿意开口说话了。说他心里愿意说的话,他太苦了,如果你愿意,常来看看他。“
我理解人为何可以熬过生活的疼痛,却熬不过精神的炼狱。我们应该友爱的,善意的在圈里圈外的生活,建立彼此之间诚信,宽容的平台。能拯救我们的除了我们自己,还有和我们一样心里需要温暖和支持的人。
平安夜,是否所有的人可以平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