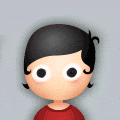和爱人在小区散步回来,我进了书房,泡上茶,一分清闲,一分健康,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。
上个月,爱人帮我寄回去玉老先生八十八岁的生日礼物,这是爱人寄的第九份礼物,八十五岁以后,最近几年,老先生不再每年都到我家小住,老先生感觉年纪大了,不方便出门,就怎么也不肯到上海来小住了,其实,真正关心你的老人,不是万不得以,他不会去麻烦你的,他宁可自己过着简单的生活,他宁可自己苦自己。
在那个安静而又古朴的小镇上,我知道,每个月的十五号,晴朗的日子,玉老先生骑着他的自行车,穿过如今已是水泥路的机耕道,过了信江河,到建行先领了他的退休金,去邮政局领他的>>>后,寄上写给我的信,再去老干局,和教育系统的老伙伴们唠叨唠叨国事,家是,十二点,去车站边他的学生的小饭馆吃上一碗水饺或是馄炖,开心时又不免帮人写写店面的招牌。
读大学的第一年暑假,我回家乡,正是收获花生的时节,清早我和母亲去地里收花生,母亲说我这几年毕竟在外惯了,还不能立刻适应家乡毒辣的日头,我们就起的很早去收花生。
才四点半钟,路上却已经是很多的行人,或拉着板车,或推着独轮车,或扛着锄头,或挑着箩筐,都是赶早去拔花生的,空气很好,草叶上还凝着露水,母亲和每一个熟识的乡亲打着招呼,父亲身体一直不好,几乎家里所有的劳作都是母亲在操持,在农村,母亲是个干活麻利,人缘极好的女人。
我记得这个早晨,记得它的美好与空气的清新,因为我在这个早上,我第一次见到玉老先生。他出现的时候,太阳已经出来了,我们已经干了一会活了。我只是照看着在旁边肯草叶的牛,隔一会捡起落在地表上花生。其它时间,我都在看从学校图书馆借回来的>合订本。
他穿着那时极为难得的白色的的确良衬衫,口袋别着钢笔,黑色咔叽布的裤子,系着部队的那种皮带,脚上是自家做的千层底的圆口布鞋,戴一顶常见的麦秸杆编织的草帽,清瘦,文雅而秀气,微笑着推着半成新的二八式自行车,左手腕戴着老式手表,黑框的眼镜,从那个小水闸上下来,在刚升起的阳光里,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。
每个人都叫他:“玉老师,赶集啊!”
我们离乡里的集市约莫三五里地,逢二,五,八的日子,就是赶集的日子,是个露天的很破旧的街道和大片的空地。
只要天气好,老先生都赶集。村里人都知道,只有我不知道。
我想我当时只所以对玉老先生第一印象如此深刻,应该和我刚从省城上大学回来有着关系,当时正是农忙季节,过往的人都是一身泥巴一身土,极少有人穿戴如此整洁。
在玉老先生的背影渐行渐远,大家的话题就转到玉老先生的身上。
“很好的先生,可惜梅花婆婆走了,条件好,说什么也不找个伴,真是难得。”村西头菊花婶娘的叹息。
“谁说不是呢,他家几个孩子都通情达理,看老吉头老伴才走两月,村里就风言风语。他都六十七了,比玉爷子还大四岁呢。”是隔壁的胖婶。
“老吉头,呸,他老子就不是个好货色,他哪能和玉爷子比,几十年,谁嚼过玉爷子半点舌头,他老吉头,那年要不躲他奶弟家,还不被人灌大粪,敢睡支书他媳妇。”
“别说了,老吉头也过来了。”村东头的叶子娘娘快速打断胖婶的话头:“老吉头,赶集啊!”
小水闸过去便是玉老先生全大队的水库了,水库边上,便是我们村的花生地,在过去,就是大片的石头岭,很平整,是整个村子收获季节晒谷子和花生的场地。
老吉头,正缓缓的走过来,国字脸,很端正,有着长长的花白眉毛。和玉先生不同,他有着严肃的脸。和大家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着就过去了。我似乎觉得他回过头,扫了我和母亲一眼。
胖婶朝叶子娘娘伸了伸舌头,转过身:“长瑞嫂子,你将来有福气,你家亮子将来是政府的人,你将来是要去省城养老的。这亮子,从小就是读书的料。吃了苦的娃,将来更出息。”
母亲抬起腰,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将来亮子能让我省心就好了,他爹那个身体啊,能去哪里,将来啊,更走不动喽。”
母亲虽然这样说,可是我还是听出了母亲心里的欣慰。
现在有时侯看着这样的场面,听着乡亲们的唠叨,我觉得熟悉而又陌生,这种感受我是后来看了路遥的>才有更深层次的体会。有时侯,我和玉老先生都会安静的坐在村子背后那宽阔的石头岭上,那是全村人晒稻谷的地方,人与人真的是很讲究缘分的。
十点半,我们干完了活,母亲在水库边上洗着农具,玉老先生赶集回来了,在边上他儿子的菜地里,摘了一把菠菜。
“玉老师,我帮你洗,免得您沾湿鞋子。”玉先生还没来得及拒绝,母亲已经很麻利的从他手中拿过菠菜。
“这是我家小三,快叫玉老师好。”
“你就是那个学了泥瓦匠又回去考大学的,不错,不错。”
这就是玉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那时真的没有想过,彼此之间会影响如此之深。
在将近十年的时间,只要有假期,我们一起散布,写毛笔字,我学会吹口琴,学会了基的填词技巧,更重要的,在梅花婆婆走后的一年后。玉老先生的脸上又开始有了微笑,我们爱看书的共同的爱好让我们有了说不出的感情,我忽然觉得自己的重要,我知道了一些我曾经陌生的中老年人的感情与内心的世界,他看我的眼睛里,经常潮湿。我学会真正懂得用心去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学会体贴和宽容。
镇上的人很爱戴他,因为他的正直,博学,和热心。毕业后,我申请回到县上教了二年书,我们家乡人的观念很淳朴,我的家人已把玉老先生当亲人一样的接纳,那年,玉老先生房子因为建高速公路而动迁,学校安排一间宿舍给老先生临时居住。学校考虑我和老先生的关系,便于照顾老校长,特别安排我的房间和他的对门,我的教学很出色,家乡的观念很传统,我们很安静的生活着,其实我很少想未来,乡里都用我的事例来教育小孩要尊老爱幼。我们自然,安静的生活,静静的教书。
玉老先生是我小学四年级德清老师的老师,玉老先生在离我家三里地的小村庄住,德清老师也教过我的父亲,德清老师和我是本村。他是因为在文革时打成右派,于是从县里的第一中学回到了村里的小学教书,一直教四年级的语文,其实据说他在县里一直是教高三的语文,那时玉老先生已经从县中学调县文教局(教育局前身)工作,是个学识渊博的人,尤其是他的书法,在县里更是数一数二,德清老师和玉老先生在教育局的大儿子玉祥是高中同学,我的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,高中只读一年就退学了,父亲的语文老师便是德清。
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我认识玉老先生以后,回去问了我的父亲才知道的。我就有点明白父亲只是个农民,兼职的大队会计,却写的一手好字,大队的书记是后来成为县司法局洪老局长女婿的雨新大伯。其时经常在院子里写毛笔字,这与当时农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,想来应该是受了德清老师的影响,父亲很少和我提起以前他读书的生活。只是父亲没有象德清老师一样,在玉老先生的影响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九十年代中期的家乡几乎很少出大学生,更何况象我这样贫寒的家庭,于是在母亲的眼里便看到了浓浓的满足,其实母亲在家几乎不怎么让我干活,因为有两个姐姐,出嫁了的姐姐要明天才能来帮忙,母亲让我在地上捡着零星的掉在地上的花生。
有的时候我想,人的性格的形成,和生长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父亲是大队的会计,以前在村小当代课老师,不怎么爱说话,身体一直不好,在我的记忆里,还是秋天的日子,父亲就开始套上他的毛线背心,在院子里拨拉他的木算盘,整理他的帐目,或是看一些旧时的小说,或是写着毛笔字,或是母亲喂完鸡以后,到地里拉扯些青草,篱笆里几只鹅便很欢快的跑过来,这时的父亲总会皱眉,父亲是个性子很慢的人,很难得发脾气,刚刚分田到户,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甩开膀子干起来,父亲还是不紧不慢的过着日子。
其实现在想来父亲不是个很严肃的人,我们兄弟姐妹有事总是先和父亲咬耳朵,再由父亲去和母亲商量,相反,因为母亲的快人快事,父亲很依着母亲。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,我从没看见父亲和母亲打架,最多也就拌两句嘴。那时农村夫妻打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兄弟姐妹四个,两个姐姐读书到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帮着干活了,手脚和母亲一样的麻利。在农村,男孩总是要被宠一些的。所以我并没有怎么去干农活。母亲和父亲的想法又不一样,父亲说,无论什么什么活,不做归不做,但是一定要会做,要懂得做的方法。母亲这一点还是很顺着父亲,只是有时看我累,特别的心疼。父亲却一直沉默。
父亲的想法到我家里出了事故我才明白,理解其中的深意。尤其是父亲的去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