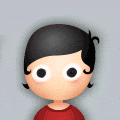年代存在,是因为着记忆。有的年代过去了,有刀凿之;有的年代,平淡无奇。如漂浮流云,风来雨去,了无痕迹,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。我们的命运,人生,生活,思忖起来,有时觉得如摆渡,从此岸到彼岸,所有岁月里的痕迹和落尘,经历里的悲悲喜喜,所有的辛劳和努力,所有的不幸与温暖,是为了在活着的财米油盐,生老病死。为了财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与苦痛。
还有一份倔强的,朴素的,不被人重视的尊严。
父辈的命运或许因为年代如此,可是仔细思忖和琢磨起来,我们又何尝不是为了这些?谁又能逃脱财米油盐,生老病死的命运呢?也因为年代的缘由,在财米油盐解决之外,我们依然对这个世界有着希冀与迷惘。由此岸到彼岸,忐忐忑忑,浮浮沉沉,我们为何要逃避和躲开?
1微笑的早晨
我没有想到我和玉老先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忘年交,到今天玉老先生还会微笑着说人和人是有缘份的。
人的心态很奇怪,老人在你的心里,会一直把他当孩子一样的照顾和心疼。我对他真正的动了感情,是在去了他家之后。或许在乡下暑假的日子真的有些百无聊赖,玉老先生每次去赶集是必定经过我家门前,但在我们熟悉之前,他一直是走村后的机耕道,在村头的小河边,经常有村里的妇女门在洗衣服,那天母亲洗完衣服让我用竹篮提回家时,我在小河边又遇见玉老先生,只是看着他微笑着和大家招呼就过去了。母亲洗完衣服又干了些家务活,便带着我去赶集,顺便出售一点自己家种的芋头种子,天气闷闷的我不怎么喜欢嘈杂热闹的场所,在家里没事情的时候,我大多数时间是在村后的枣树林里看书。那天因为母亲要推独轮车,还要到供销社买一点化肥,母亲不认识字,所以希望我陪在身边。
在集市上办完一切事情时,走在回家的路上,天下起了雨,在跑回家的路途中,我忽然看见玉老先生在马路边的小店里避雨,看样子很是着急,那天说不上是为什么,我回家后就拿了把布伞,返回了,玉老先生很是意外,也很是感激。后来他告诉我,当时他真的很感动,因为我当时自己身上都全是湿的,好在还是早秋。没什么大碍,先生说如果他淋雨,是肯定要感冒的,后来,玉老先生赶集经过我家门口,年纪大了便容易忘事,他老是惦记着要还那伞给我,父母亲总是笑着说没事。有时候,玉老先生也会在我家的小院里坐一小会。和父母聊几句家常。
又一个赶集日回来的中午,玉老先生经过我家门口,执意要我和他一起去他家拿伞了。玉老先生的眼睛很好,左耳却不是很灵光,有时候没听清,便看着我呵呵的笑。
走过长长的机耕道,右拐上了小水闸,视野便非常的开阔,方圆约五里地的水库,玉老先生告诉我,这是他三儿子小玉承包的水库,养鱼,我心里就有些纳闷,看他好象书香世家,怎么会有养鱼的儿子。
玉老先生家在村头的第一排房子,门口没有围墙,只是圈了一圈说不出名字的小灌木丛的篱笆。篱笆外边是水稻田。厨房后面是约五分地左右的小水塘,是他三儿子小玉在过年节时临时,水库的鱼打捞上来后,水塘是用来周转鱼的地方,远近有些鱼贩会在大清早来收购新鲜的鱼。
那天我和玉老先生到他家的时候,已经是快要中午了,玉老先生放下自行车,解下车后坐上一个大大的蛇皮塑料编织袋,取出一合牙膏,还有约一斤排骨,一把青菜,我忍不住笑了,这么大的口袋只放这么一点东西,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协调,有些滑稽。他执意要留我吃饭,我到他的房子后面的水井里去打水洗青菜,两栋平房,他的二儿子住靠东边一栋,三儿子小玉住西边。南方农村的房子和北方不同,是坐北朝南。进门是大大的堂屋,招待客人和吃饭用的,中间放一大的八仙桌,中堂上挂山水画或主席像,两边是对联,堂屋东西两侧是房间,其中东西两间房也各自从中间用墙隔开,一般分家前家长住东边,分家后则长子住东间,玉老先生不怎么讲话,他住的地方是二儿子的半间西间房,却又要了三儿子半间西房,放了碗橱柜子,他的烧饭的地方就是三儿子的走廊一角,烧的是煤球炉子,简易的锅灶,一个用锡皮纸补过的脸盆放在靠近走廊柱子的石墩上。大儿子玉祥住村尾最后一排,是老式的两层木结构的房子,背后便是水库和大片的石头岭。玉祥在老先生退休时顶职当了老师,后调辅导站任干事。
中午是我烧的饭,切的细丝般的青菜,因为他的牙不好,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他的三儿子的八仙桌上放着好多的红纸,大的碟子里是倒的满满的墨汁。
玉老先生告诉我,他平素除了天气好三天赶一次集市,基本不出门,就在家里写对联,到了过年时,附近村里的人们都到他家拿对联,他从不收钱,后来村里人过意不去,他才收取一点买纸张的钱。他说他没有女儿,也没什么地方可去,赶集是为了骑自行车锻炼身体。
说实话,没去他家之前,我是想不到他的房间是如此的简陋。而且零乱,雕花的老式木床,有着阁楼式样的书桌,堆满了杂志,文言文版的《古文观止》,《唐诗三百首》还有笔筒里大大小小的毛笔,一本我也很喜爱的《辛弃疾词文选注》,他说他那摆在桌角落的煤油灯有上百个年头,虽然普通,却是不舍的丢弃,总会怀念当年灯下苦读的日子。灯罩是当年不小心打破,走了五十多公里去古镇上才买到原配。虽然凌乱,在老先生的叙述里我忽然觉得特别的安静。觉得很多古朴的东西在里头。让人留恋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同志这回事。那时,农村大都用大的木头打制的尿桶,在老先生的衣柜与床头之间,好象是红木的刻了花纹的马桶。非常的笨重,还经常的不盖盖子。靠窗的地方放着竹制的可以放下也可以支起来的躺椅。已经很旧了。堆满了已经换下来要洗的衣服,老先生说,等农忙结束,就拿给大儿媳妇洗。
现在想来,第一次去我就观察的比较仔细,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安排。之后很多年,我就在这间小屋里。度过很多简单的幸福时光。这种恬淡与安静在后来的城市高楼大厦,钢筋水泥建筑里成了如烟往事。